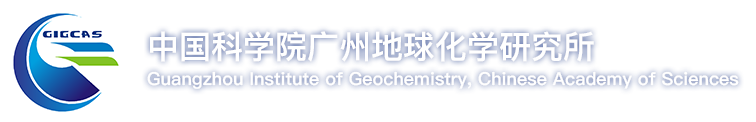碳酸盐的“地心游记”——它经历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撰文:高名迪 王煜 袁斯来
1864年,儒勒·凡尔纳已经36岁了。他终于拿到一位知名出版商的长期合同,为其写作系列作品“奇异的旅行”。
于是,那年冬天,法国人读到了一段奇异壮丽的探险故事——讲述德国地质学家李登布洛克的《地心游记》。
在一张泛黄的牛皮纸上,李登布洛克发现了冰岛炼金术士记载的深入地心的方法。他带着侄子和向导,从冰岛的火山口出发走入地壳之下,开启了一段奇幻之旅。
李登布洛克目睹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景观,庞大复杂的洞穴、潮汐起伏的地下海洋、中生代的蘑菇森林以及史前动物的残骸。一系列冒险后,三人乘着火山喷发的气流再次回到地表。
凡尔纳150年前的想象瑰丽而浪漫,但显然不符合现代科学。
即便在2025年,进入地球深部仍是科学界未能完成的任务。半个世纪过去,最深的人造井科拉超深钻孔,也只抵达12.2公里的深度——甚至没能穿透地壳,离地幔还有20多公里。
但地球还是给人类留下了探索深部世界的路引。
有赖于活跃的板块运动,地球深部岩浆活动将一些深部信息碎片带回地表。金刚石正是碎片中最忠实、最珍贵的记录者。
金刚石在生长过程中,一部分会包裹周围的矿物、流体或熔体形成包裹体。地质学家偏爱这类金刚石(如图1所示,左图为含包裹体的金刚石,右图为纯净金刚石)。正是这些看似“杂质”的包裹体,通过分析其化学成分与同位素组成的细微差异,便可为我们揭开地幔深处尘封的往事。

图1. 左图:含有矿物包裹体的金刚石(产自巴西Juína);右图:纯净的金刚石(产自南非Cullinan)。图片来自于Shirey et al.(2024)。
地质学家依据氮含量与包裹体特征,将金刚石划为了岩石圈金刚石(lithospheric diamond)和超深金刚石(superdeep diamond,or sublithospheric diamond)两种类型。前者形成于小于200公里深的岩石圈,且在自然界中占比超过99%;而不足1%、却能记录深至下地幔(超过660公里)信息的超深金刚石,则如星辰般散落于南非、巴西与几内亚等几个地方(图2)。

图2. 全球超深金刚石分布,其中多数来源于南非与巴西。图片来自于Shirey et al.(2024)。
同位素研究证据表明,超深金刚石和包裹于其中的“杂质”物质主要来源离不开地表碳酸盐(e.g.,Burnham et al.,2015)。这意味着,板块俯冲作用会将巨量的地表碳酸盐带入岩石圈之下,巨量碳酸盐被带入了岩石圈之下,直抵金属Fe稳定存在的深部地幔。在那里,碳酸盐中的C4+被还原为0价的金刚石或负价态的Fe-C合金(carbide),而地幔中的金属Fe则被氧化为Fe2+乃至Fe3+,进入到“杂质”包裹体中。这个反应将活泼的碳酸盐冻结成稳定的金刚石,地质学家称之为“氧化还原冻结反应”(redox freezing)(e.g.,Rohrbach and Schmidt.,2011)。
然而,这场碳酸盐的“地心旅行”结局如何?它们是被悉数冻结,还是有幸存者以碳酸盐或CO2的形态重返天日?仅凭超深金刚石这些信息碎片尚不足以描绘全貌。
既然信息有限,最好的办法就是复刻一遍碳酸盐的“地心之旅”,再回头看看这些碎片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们利用多面砧压机这一“地球深部环境模拟装置”(如图3所示),用实验重现了碳酸盐与含Fe的还原性地幔在300-600公里深处相遇的场景。

图3. 左图: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高温高压实验地球科学中心2500吨Sakura多面砧压机。右图:实验样品组装。将装有样品的八面体(右上)放置于8块有截角的碳化钨构成的八面体空间中(右下),然后在多面砧压机中挤压8块碳化钨块构成的立方体,即可在样品内部模拟深部地幔的高压环境。
我们的实验发现,无论碳酸盐是否被完全还原冻结,其与地幔的反应总会形成一种名为超硅石榴子石(majorite)的矿物。而当碳酸盐被彻底冻结为金刚石及Fe-C合金时,常伴有铁方镁石(ferropericlase)的生成。
巧合的是,超硅石榴子石与铁方镁石正是超深金刚石中最主要的两种包裹体“杂质”。
于是,我们对比了实验获得的“人造矿物”与巴西和南非两个最主要超深金刚石产地中的天然矿物包裹体。成分对比结果显示:当碳酸盐未被完全还原时,产生的超硅石榴子石总是具有高镁、低钙、低钠特征——和南非超深金刚石中超硅石榴子石包裹体成分特征契合。而当碳酸盐被完全还原冻结后,超硅石榴子石呈现出相对高钙、高钠特征,且矿物中的钙与钠分别会随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与升高——完美符合巴西超深金刚石中超硅石榴子石成分变化(如图4所示)。
这似乎意味着,在从深部地幔返回地表归途中,碳酸盐在南非部分得以“幸存”并重见天日,而在巴西则被彻底冻结为金刚石与Fe-C合金。

图4. 实验产物超硅石榴子石与天然超深金刚石中超硅石榴子石包裹体成分对比。蓝色实心圆为有碳酸盐残余(氧化)的实验数据,橙色为碳酸盐被完全冻结(还原)的实验数据。蓝色空心点为南非超硅石榴子石包裹体数据,橙色为巴西包裹体数据。
铁方镁石的证据再次证明了我们的推测。通常,这种矿物只稳定存在于下地幔。但是,多数巴西超深金刚石中铁方镁石包裹体相比于下地幔铁方镁石有着更低的Mg含量——它们被认为来自于不足660公里深的上地幔。而我们的实验证明:在碳酸盐被完全还原冻结的同时,低Mg铁方镁石可以出现于上地幔。
为何会有如此迥异的命运——这和温度相关。
继续分析实验结果,我们发现在正常地幔温度下,碳酸盐会持续被还原消耗。但当地幔热对流遭遇更炽热的地幔柱扰动时,Fe3+得以从地幔矿物中释放出来。于是,在Fe3+的缓冲下(C+4Fe3+= C4+ + 4Fe2+),一部分碳酸盐得以在还原地幔的考验中幸存,并最终通过火山作用重返地表。
只是,这些都是实验猜测。碳酸盐是否在真实世界中,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于是,我们做了板块重建工作验证。恰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温度起了关键作用。

图5. 4亿年(400 Ma)至今古板块重建。黄色圆形区域为地幔柱影响区域。
4亿多年前,当俯冲板片携带的碳酸盐深入巴西下方地幔时,彼时南美大陆并未受到地幔柱侵扰。因此,碳酸盐被完全冻结为金刚石,并随着地幔对流拼贴至巴西岩石圈底部(Timmerman et al.,2023)。这些承载着远古地球脉动信息的金刚石,在随南美大陆漂泊超过3亿年后,于9000万年前藉由火山喷发重见天日,为人类揭开了地球深部涌动的神秘面纱。
在另一个时空,南非大陆从大约2亿年前开始持续受到下方地幔柱的“炙烤”。当碳酸盐潜入南非大陆下方,一部分被冻结为超深金刚石,更多的则在地幔柱的助推下逃逸。未被束缚的碳酸盐携带着金刚石,不仅在南非大陆引发了中生代广泛的火山活动,更在奔向地表的途中,于南非大陆之下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由此,一场更为宏大的地质变迁拉开序幕:以南非为支点,古老的冈瓦纳大陆分崩离析,非洲、南美、南极与印度大陆各自漂向远方,塑造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地球的样貌。

图6. 非地幔柱与地幔柱条件下碳酸盐与地幔反应过程模式图。
当严谨的科学探索告一段落,李登布洛克脚下那片地底深海依然令人遐想:水面一望无际,居住着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渺无人烟,荒凉得可怕。他站在岸边,既惊愕又恐惧地赞叹,“ 仿佛身处天王星或海王星这样遥远的星球,看到了地球人的本性所难以体验的奇观。”
论文相关信息:Gao,M. (高名迪),Wang,Y.,(王煜)*,Foley,S.,Xu,Y-G (徐义刚).,2025. Variable mantle redox states driven by deeply subducted carbon. Science Advances,11(21),eadu4985.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u4985
参考文献:
Burnham,A.D.,Thomson,A.R.,Bulanova,G.P.,et al.,2015. Stable isotope evidence for crustal recycling as recorded by superdeep diamonds. Earth Planet. Sci. Lett. 432,374-380.
Rohrbach,A.,Schmidt,M.W.,2011. Redox freezing and melting in the Earth’s deep mantle resulting from carbon–iron redox coupling. Nature 472(7342),209-212.
Shirey,S.B.,Pearson,D.G.,Stachel,T.,et al.,2024. Sublithospheric diamonds: Plate tectonics from Earth's deepest mantle samples. Annu. Rev. Earth Planet. Sci. 52,249-293.
Timmerman,S.,Stachel,T.,Koornneef,J.M.,et al.,2023. Sublithospheric diamond ages and the supercontinent cycle. Nature 623,752–756.